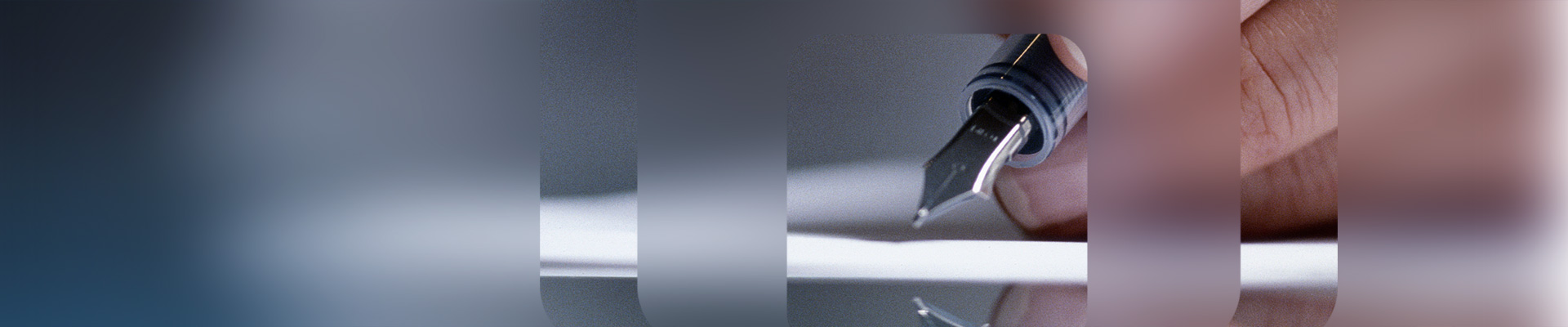代孕子女亲子关系认定问题研究
一
厦门市张某所生孩子因意外去世,其妻又过了生育年龄,但夫妻俩很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张某经过多番周折找到了李某,夫妇俩与李某商定由她来为他们代孕。李某怀孕期内由张某承担所有费用,并承诺孩子出生并交付后给予李某丰厚的报酬。但孩子出生后李某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交付孩子,张某也就不再支付抚养孩子的费用。后代孕者李某便将张某告上了法庭,要求张某支付孩子的“抚养费”。本案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审理最后判决将非婚生女交由给李某抚养,张某作为孩子的父亲,每月承担孩子抚养费3200元,支付至孩子18周岁止。外籍华人陈某因为妻子不能生育,与妻子商量后决定用捐赠者的卵子和自己的精子进行受精,后找到一名家住常德市的王某育龄期妇女代孕,并与王某签订了代孕协议,约定由陈某承担王某代孕期间的所有费用,并向王某支付代孕费用10万元,孩子生下来后交给陈某夫妇抚养。后王某产下一名男孩,但却反悔不肯将孩子交给陈某夫妇。后双方协商不成陈某夫将王某告上法庭,要求孩子归陈某夫妇抚养。本案经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最终法院将孩子的抚养权判决给了陈某夫妇。
以上是关于两个法院审理两个关于代孕子女抚养权纠纷案件的不同判决:一个法院认为代孕合同有违公序良俗,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该合同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判决代孕母亲取得孩子的抚养权;另一个法院则认为代孕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代孕协议有效。判决将代孕子女抚养权按协议约定,归代孕委托人所有。代孕子女的抚养权到底应属于哪方?不同法院对代孕协议效力判法不一,我国对代孕的规定只有一部行政规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并无法律法规层面上的规定,缺乏统一裁判标准,因此值得我们深思。
二不同模式的代孕法律规制对亲子关系认定的影响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伦理观念以及法律文化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在关于代孕子女认定方面大致有以下几种学说:
(一)“分娩说”,即“谁分娩,谁为母亲”,由分娩事实决定孩子母亲,再看母亲的合法婚姻关系来推定孩子的父亲。
(二)“血统说”,通常又被人们称为“血统主义”或“基因说”。即依据血缘关系,精子或卵子提供者成为孩子的父亲和母亲。
(三)“契约说”,又称“人工生殖目的说”,认为难以对分娩事实和血缘事实在生育中的贡献做出比较,又基于代孕子女是委托夫妇与代孕母根据代孕约定而出生的,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双方的意愿来确定委托人为代子的法定母亲。
(四)“子女最佳利益说”,即从最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教育的原则出发,以子女利益为最大利益考量来确定代孕子女的法律父母。
其实不管采取以上无论何种学说,在司法实务中都会涉及到代孕协议效力和代孕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代孕协议是否有效一直是国内学者争议较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代孕协议违反了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公序良俗原则,而且对家庭关系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是无效合同;也有学者认为代孕协议有效。代孕协议是代孕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协商签订的协议,未违反合同自由原则,双方自愿签订合同,约定代孕子女的亲权,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围。
对代孕子女地位认定的不同理论学说投射到世界各国的司法实务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代孕法律规制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模式,而这个模式直接影响了在法律亲子关系上的认定。现今国家主要采取的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 完全禁止型,是指国家在立法上禁止各种形式的代孕,在民法上规定代孕协议无效,在刑法上处以刑事惩罚。完全禁止代孕的国家有德国、法国、日本等。完全禁止型模式国家在亲子认定中都无一例外的以代孕母作为认定标准,是基于权利义务相适应角度的考量。禁止代孕虽然简单方便,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回避代孕产生的亲子关系认定的问题,剥夺了代孕子女应该享有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二)有限开放型,即国家允许某种类型的代孕,而禁止其他类型的代孕规制模式。实行有限开放型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对代孕根据不同类型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即允许在符合特定条件下的代孕行为,并承认代孕协议的合法效力。英国、荷兰、泰国和中国香港等都采取了这一模式。但就算在允许有限开放代孕的国家,在立法上也都会对代孕主体的条件、协议的效力、社会公益团体的管理等都有一定的限制性规定。
(三)非统一规制型模式。世界上一些联邦制国家,各州或区除了尊崇联邦统一的宪法外,都会有自己制定法律的权利。在代孕立法上没有作出统一规制,而交由各个地方自行解决,采取这一模式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等。制定或实施更契合本地区伦理道德和实际需要的规制策略,但同时也会引起各地方因立法不一致发生冲突的问题。给有意图从事商业代孕活动的人提供了规避法律的机会,不利于一个国家法制的统一。
(四)近乎完全开放型模式。禁止商业代孕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做法,学界的观点也相对比较统一。近乎完全开放型模式并非是指完全支持代孕,而更多是说对代孕不加以明确的法律禁止,而允许放纵甚至泛滥的规制模式。如印度、俄罗斯、墨西哥等国家就是近乎完全开放型国家的代表。近乎完全开放型的法律规制模式只在当今少数几个国家实行,商业化代孕客观上将代孕母作为生育的工具,有违公序良俗,严重损害了人的尊严,法律必须禁止。
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与创新,不论何种模式下的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都需要综合社会、法律、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问题,平衡各方权益才能作出更好的判定,这也并不是采纳某一种学说或采取何种模式就能一揽子解决的,但对我国代孕子女亲子关系的认定具有借鉴意义。
三
我国现行立法对代孕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规制策略,即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技术。对因代孕而产生的子女关系认定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对代孕的法理和伦理的争论一直经久不息。文章开头提到的几例抚养权纠纷也都是因代孕而产生的,虽然我国全面禁止代孕,但却回避不了代孕产生的亲子关系的认定问题。建议我国在坚持“分娩为母”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来规制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问题,同时在当下利用现有法律框架及司法实践中的判例运用来解决该问题。
(一) 建议通过立法解决代孕亲子关系的确认
从国际通例来看,无论该国对代孕持有何种态度,大多都会在立法上对该问题予以规定,如法国、英国、美国等都采用法律形式规范代孕生殖问题。而我国现阶段仅有一部原卫生部颁布的行政规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该办法属于卫计委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并没有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之外的其他机构与公民作出任何规范,其对代孕的禁止范围有限。对于代孕中介机构、委托代孕者等其他社会主体则无任何规定。该办法只是一部行政规章,法律效力层次相对比较低,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获得有效适用,它也无法对代孕及其因代孕而产生的相关问题作出更为全面的规制。鉴于以上原因,建议我国出台一部效力层级更高的规制代孕的行政立法,如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的《人类辅助生殖法》或国务院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管理条例》,并在该法或条例中明确就代孕作出禁止性规定;同时对代孕的禁止范围扩大到所有从事代孕活动的机构与人员。在行政立法上,参照新修订《环保法》的做法,加大处罚违法者成本,以遏制非法代孕的蔓延。在民事立法上,建议我国应在《合同法》或《民法典》中也明确代孕协议的非法性,并对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对代孕子女应有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
(二)基于含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关系的类推
2011年上海男子罗某因妻子陈某不能生育,后通过以购买卵子的方式请人代孕,后得到一对双胞胎罗甲和罗乙。三年后罗某不幸因病去世,得知真相的罗某父母诉至法院,要求取得两孩子的监护权。一审法院以陈某与罗甲罗乙不存在血缘关系,亦不存在拟制血亲关系为由,罗甲罗乙的代孕母又不明的情况下判定罗某父母获得监护权。陈某不服该判决,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以类推适用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关系的法律适用及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运用,认定陈某与罗甲罗乙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撤销了一审判决,驳回了罗某父母要求取得罗甲罗乙监护权的诉讼请求。
该案中二审法院的审判思路是: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罗甲、罗乙确系代孕母所生,罗甲、罗乙系罗某婚外所生,故属于“非婚生子女”。但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因此《婚姻法》第二十七中的继子女范围也应包含非婚生子女。法院在判决书中还归纳出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的成立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主观意愿;二是事实行为。至于子女的出生时间在缔结婚姻之前还是之后,并非《婚姻法》规定的认定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实质要件。本案中罗某甲、罗某乙出生后一直随罗某、陈某夫妇共同生活已有五年,陈某已完全将两名孩子视为自己的子女,并履行了作为一名母亲对孩子的抚养、保护、教育、照顾等诸项义务,故应认定双方之间已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其权利义务关系应当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确认陈某与罗甲、罗乙之间形成拟制的母子关系。同时从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年龄、身体状况以及精力、收入等各种因素的考虑,以孩子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据此撤销了一审判决,赋予了陈某监护权。二审法院摒弃了代孕是否合法的偏见,结合案件事实,运用相对慎密的法律论证思维定的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判例,也不失为当前法律无明确规定,在代孕纠纷下代子关系确认及监护权纠纷的的一种解决途径。
(三)“事实上监护或扶养关系”的司法实践参照
在父母子女的关系认定上,如果存在血缘关系毫无疑问就可认定为父母子女关系。我国法律上还规定了一种拟制血亲的关系,《收养法》、《婚姻法》中规定了两类拟制血亲:一是养父母子女关系;二是在事实上形成了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上述因代孕产生的监护权纠纷法院的论证点就落在是否成立拟制血亲关系。如果代孕产生的子女,在法律认定上能类推适用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或养子女,那么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就可解决该问题。上述案件的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论证可陈某与罗甲、罗乙不存在拟制血亲的继子女关系,也不存在收养关系。但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不存在事实收养关系,但存在继父母子女关系。试想如果本案中的代孕母已死亡或一直无法找到,而陈某实际履行了抚养、照顾、教育等义务,基于未成年人成长利益考虑,司法者又能否赋予依据“事实上监护抚养关系”而把监护权判给委托代孕人呢?
(四)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子女最佳利益”是指以最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为标准来认定代孕子女法律上的父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中都有确立了“保护儿童利益”的原则,上述案例二审法院的判决也是在以上原则的指引下作出的。在本案中法院除了认定了陈某与罗甲、罗乙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关系外,原被告双方监护能力的判定也是其在裁决程序中需要认定的实体问题。但如上述案例中,假设出现代孕母在孩子出生后反悔了,拒绝交出孩子,出现代孕母与委托夫妇争夺抚养权的案例;亦或孩子出生后由于有缺陷或疾病,委托夫妇反悔,不愿抚养孩子了。在这种情况下为解决纠纷,法院就可根据该原则为判断标准,综合考虑双方经济能力及必要的物质条件,从孩子对生活环境及情感的需求、家庭结构完整性对孩子的影响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来做出判决。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是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和基本人权的具体体现。法规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不近人情的,但它追求正义与良善的内涵是永恒不变的。
代孕技术的出现, 给那些因自身缺陷而无法生育的夫妻带来了希望,但同时也使建立在自然生殖基础上的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无从适应,突破了传统民法上的亲子身份认定规则。代孕是否合法的问题,并不影响代孕子女出生后在法律上的地位及应有权益保护的。和自然生殖出生的孩子一样,他们的人格尊严和身份关系也应受法律的保护关于代孕及相关问题的法律规制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目前对代孕的禁止也不代表将来一定不会进行有限度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