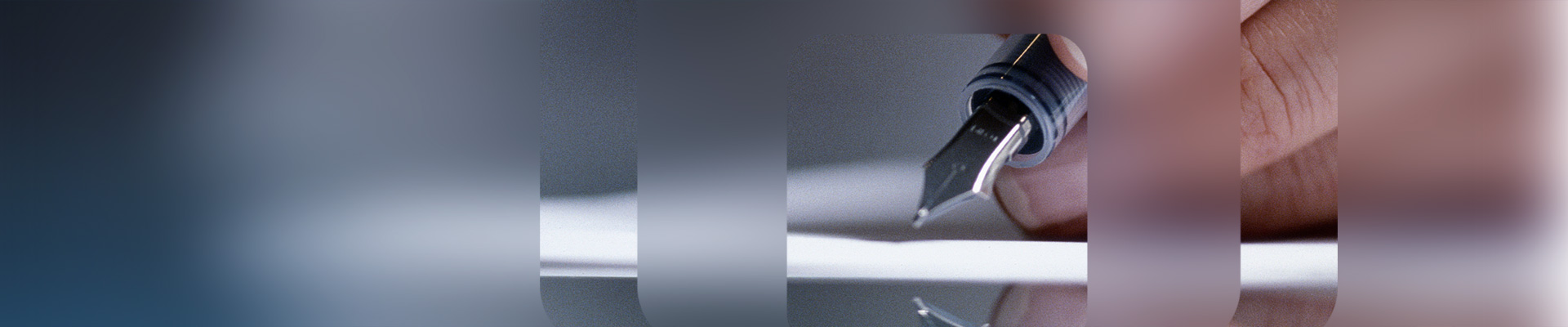如果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健全,张扣扣就用不着辩护词了
近日,张扣扣杀人案在社会上引起热议。不少人认为张扣扣杀人最根本的动机是为母报仇,张扣扣既是本案加害者,也是二十二年前母亲被伤害致死的受害者。由于被害人保护机制的不完善,社会矛盾得不到有效化解,导致原始的同态复仇死灰复燃。这些观点虽有失偏颇,但当前如何健全刑事被害人保护机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切实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和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现状
一关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指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块“短板”。在立法方面,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制定,到1996年修改,再到2012年修改,虽然对被害人的立法保护水平在逐步提高,但仍不完善。
1979刑诉法是我国第一部刑诉法,限于当时的经验积累和立法水平,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不足在所难免;1996刑诉法修改的重点和亮点是被害人权利保护,该法将被害人从与证人等同的“诉讼参与人”地位提高到与被告人等同的“当事人”地位,但由于不够具体和可操作性不强,总体上刑事被害人还是“有当事人之名,少当事人之实”;2012年刑诉法修改,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期望新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作更进一步的规定。然而2012刑诉法修改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几乎没有新的加大被害人保护力度方面的条款。
相反,之后“两高”的新司法解释中反而对被害人权利作了一些“倒退”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6条,改变了过去将被害人代理人与辩护人在阅卷权方面一视同仁的规定,对被害人代理人增加了“经人民检察院许可”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6条中,对辩护人的阅卷权规定为“应当允许”,而对被害人代理人的阅卷权,作了“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和“也可以”的限定。如此厚此薄彼,应验了学界关于“刑事被害人是被现代司法遗忘或冷落的人”的说法。
二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司法机关在通过刑事诉讼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追究因被告人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在立法上,我国1979年以来制定及修改的三部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其法条规定基本一致,条文内容逐步细化。从现行立法情况看,相对于刑事被害人制度的松散型立法结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结构显得比较紧凑,其主要集中于刑事诉讼法第七章(即第99条至10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12月20日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2年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六章(即第138条至164条)之中。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最高院2012年刑诉法司法解释的施行,之前一些涉及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及批复等基本都已经失效,比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批复》等。
虽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相对比较完整,但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然而,最高院2012年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38条却将赔偿范围限定为“人身权利受到侵犯”或“财物被毁坏”的“物质损失”。该司法解释第139条还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该司法解释不仅将间接损失和精神赔偿排斥在外,还缩小了物质赔偿的范围,影响了对被害人权利的实质保护。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代理和附带民事诉讼代理的现状
一侦查阶段的律师代理制度及代理实践的缺失
1.代理律师的身份缺失。现行法律没有规定代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具体工作职责,因此代理律师没有适当的法律身份参与侦查过程。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代理律师在此阶段的具体参与权及陈述意见权、知情权等必要权利,使得代理律师难以名正言顺地帮助被害人,也难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2.律师知情权的缺失。由于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被害人及其代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加之侦查机关传统意识的存在,对代理律师的询问和沟通往往会拒之门外,这使得代理律师无法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提出建议和监督,影响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
3.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缺失。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有些证人可能被侦查机关遗漏,有些证人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如实向侦查机关作证。同时,有些证人可能会因为同情被害人,或在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劝说下会如实向侦查机关作证。但由于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不允许被害人代理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必要调查和会见证人,因此也会影响到侦查机关全面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从而也影响了事实真相的查明。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律师代理制度及代理实践的缺失
审查起诉阶段是衔接侦查阶段与审判阶段的重要诉讼阶段。检察机关能否充分地行使指控犯罪的职责,会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处理结果。对此,被害人代理律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助和监督检察机关及时有效行使职权。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代理律师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
1.现有法律规范过于原则且操作性不强。虽然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被害人代理人的意见,但由于没有具体规则的指导和约束(例如听取意见的方式、听取意见的记录和归档、检察机关未合法听取意见的法律责任等),使得检察机关对于被害人及代理律师的一些合理请求往往仅作表面应付,代理律师在此阶段的工作也没有主动性和实质性,无法产生积极有效的代理结果。
2.代理律师的阅卷权受到限制。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8条只规定了辩护人的阅卷权,对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却未作规定。最高院在2012年刑诉法司法解释第57条中规定了诉讼代理人的阅卷等相关权利参照适用辩护人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6条,对诉讼代理人阅卷权增加了“经人民检察院许可”的限制,在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的规定》第6条中,对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作了“应当允许”的规定,而对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却作了“经许可”和“也可以”的双重限制,影响了被害人代理律师充分行使权利;
3.缺乏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有效救济。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了被害人对于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对复议决定不服的还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但在实践中,这种事后救济的方式很难达到积极的效果。因此,有必要采用听证等方式对不起诉决定进行事前的听证,并赋予被害人代理律师协助被害人在听证中发表意见的权利,以更好的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法院一审阶段中被害人代理制度及实践中的问题
法院一审阶段对于被害人代理律师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代理阶段。在法院一审阶段中,被害人代理律师可以协助检察机关对被告人进行指控,揭示案件的事实真相,提出法律的适用意见,全力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比比皆是。一方面在于法律的规定还不够完善,没有赋予被害人代理律师充分具体的权利保障;另一方面则在于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承办人受传统“国家追诉主义”的影响,使被害人代理律师的诉讼权利没有很好落实。有不少办案人员认为,行使控诉职能只是检察机关的事情,并不需要被害人代理律师来越俎代庖。因此不少法官会限制代理律师的权利,使本来就很少的法律保障大打折扣。因此,代理律师原本可以大有所为的一审阶段,却成为一条荆棘之路:
1.独立诉讼地位的缺失。现行刑诉法虽然将被害人纳入“当事人”地位,但现行法律制度没有规定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独立的诉讼地位及辅助控诉权。被害人代理人与公诉人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影响到了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效率和力度。由于没有建立起被害人诉讼代理人与检察机关之间相互协作相互监督的制度框架,检察机关在实质上往往并不希望代理律师参与公诉活动,代理律师也很难对检察机关的公诉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2.被害人及代理律师的庭审权利缺乏可操作性。现行法律对被害人代理律师在庭审中的权利规定过于原则,缺少可操作性的细化规则和救济规则。代理律师难以在庭审中通过补充证据、询问证人、发表陈述意见、进行法庭辩论等方式来表达其对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的意见。而且从法律制度而言,我国被害人代理律师的诉讼地位远远不及辩护人,法庭上审判人员限制被害人代理律师发问、举证和辩论的情况颇为常见,影响被害人权利的充分实现。
3.被害人代理律师意见未载入判决书。 由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文规定,故在各个法院判决书中,既不列明律师的被害人代理人身份,也不对被害人及代理人的意见及采纳情况载入判决书。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写明代理律师的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身份和民事赔偿意见。因此,应当依法规范法院的裁判文书,客观体现被害人代理律师参与庭审的情况和参与意见,以督促法院对刑事被害人代理律师代理意见的重视,更好地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四法院一审阶段中附带民事诉讼代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其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损害赔偿而进行的诉讼。在法院一审阶段,被害人可以就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的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在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上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诸多不足:
1.赔偿损失的范围过小,且只赔偿物质损失,不赔偿精神损失。在杀人、伤害、抢劫、强奸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犯罪分子理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但是依据我国现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害人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现最高院2012年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38条第2款对此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而在实践中被害人及近亲属主张赔偿精神损失“告状无门”。
2.在物质赔偿中,只赔财物被“毁坏”的损失,不赔财物被“占有、处置”追赃不足的损失。根据最高院2012年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39条“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物质损失赔偿只赔财物被“毁坏”的损失,不赔财物被“非法占有、处置”的损失。这一规定对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的“物质损失”赔偿范围作了缩限解释,影响了被害人赔偿权的实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8月出版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61辑刊登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倾向性意见,认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不能弥补损失,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该倾向性意见与最高院2012年刑诉法司法解释的内容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告状无门”。
3.在人身损害赔偿中,对具体赔偿范围的列举不明确,造成实践中的“各行其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和项目,以往实践中根据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处理,并无大的争议。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对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还是物质损失的定性前后反复,但实践中并未影响被害人及近亲属获赔。但最高院2012年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5条第2款“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的规定颁布施行后,不少法院认为,该司法解释中未列明死亡赔偿金和残废赔偿金,故不属于法定赔偿范围,在调解和解不成的情况下应判决不予赔偿。以致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杀害、伤害、抢劫等案件的被害人无法获赔的情况。
五法院二审阶段中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不足
1.法律未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虽将被害人定位为“当事人”,但没有赋予被害人以上诉权,这一做法在理论界争论很大。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应当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以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事实上,现行法律规定的被害人的抗诉申请权,被采纳的情况相当有限,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检察机关对被害人的抗诉请求不予重视和不予支持的情况,导致了被害人及其代理律师无法直接参与到二审程序中,无法继续维权。而且,对于检察机关不予抗诉的决定,被害人无法通过事前听证、事后复议等方式从制度上得到相应的救济,严重地影响到了被害人及其代理律师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
2.二审不一定开庭的审理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法院可以对事实清楚的一审案件不开庭审理,但事实上是否“事实清楚”并不是未经开庭就能判断的。虽然现行法律规定对不开庭的案件应当听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但是这一规定过于原则,没有给以审判机关必要的制度约束,而且也没有给予被害人及其代理律师充分细化的制度支持,因而在实践中往往未能严格执行。而且仅听取意见是不够的,无法与开庭一样起到保障被害人权益的作用。
3.对严重剥夺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情况缺乏有效制约措施。现行法律对司法机关故意不告知被害人案件处理进展情况,对严重剥夺被害人诉讼参与权的情况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实践中,有的司法机关对应当通知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因图省事怕麻烦故意不告知不通知,等被害人知晓时一审已经结束。最高院2012年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61条规定在二审期间提起附带民诉的,法院只能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被害人在刑事裁判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一规定不利于杜绝侵犯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情况再次重演。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应将此类情况确定为严重程序违法,应当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判。
综上所述,刑事诉讼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护难的问题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取得理想效果难的问题,既有立法滞后的原因,也有执法不严的问题。如何健全和完善刑事被害人保护机制,避免悲剧重演,这也是张扣扣案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相关论文和著作,以供查阅:
1.《当前刑事被害人代理与附带民事诉讼代理的困境及对策》论文,作者:朱加宁、徐鹏,《法治研究》2016年增刊第2期;
2.《刑事诉讼被害人代理与附带民事诉讼》,朱加宁、叶连友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