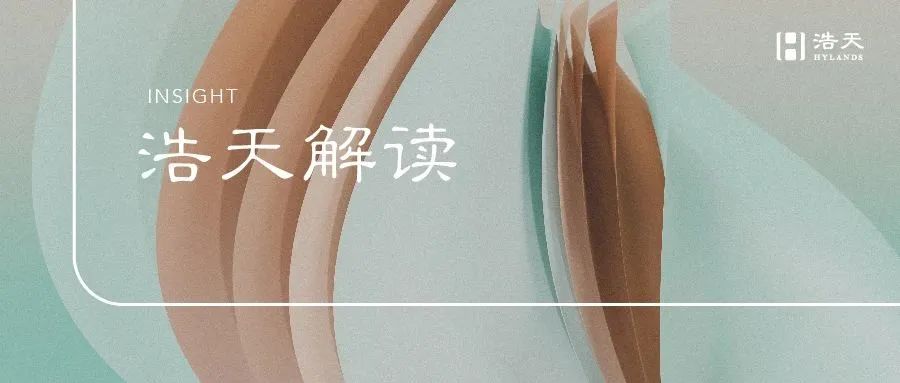对赌协议纠纷中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问题研究
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机制或估值调整协议。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的规定,对赌协议是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
对赌协议在我国实践中主要有三种场景:一是PE/VC投资过程中的对赌;二是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中的业绩补偿;三是中国企业并购海外标的时或有对价(earnout)的安排。[1] 司法实践中的对赌协议纠纷主要涉及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这两类约定,在合同签订方面,除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外,投资方与融资方之间通常还会以补充合同的形式约定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等对赌内容,或者签署担保合同为对赌义务提供担保。若上述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仲裁协议,而补充合同或者从合同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当补充合同或者从合同中的条件成就时,投资方能否依据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仲裁协议提起针对补充合同或从合同的仲裁程序,亦即,在此种情况下,增资协议、股转转让协议等主协议中的仲裁协议的效力,能否扩张到补充协议或从合同?
本文旨在对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司法裁判观点进行梳理和分析,厘清对赌协议纠纷中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17年修正)》(以下简称“《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包括以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据此,仲裁协议原则上要求书面形式,目的是确保当事人之间确实达成了合意。[2] 因此,当补充合同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时,有观点认为,投资方与融资方是基于补充合同的对赌内容发生争议,鉴于双方并未就该等内容约定仲裁,故应视为双方之间没有仲裁协议。即,主合同的仲裁协议不能约束补充合同。[3]
司法实践中,对于没有约定争议纠纷解决方式的补充协议可否适用主合同的约定,法院认为关键在于审查主合同与补充协议之间是否具有可分性。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报案例(2015)执申字第33号执行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如果主合同与补充协议之间是相互独立且可分,那么,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对于两个完全独立且可分的合同或协议,其争议解决方式应按合同或补充协议约定处理。如果补充协议是对主合同内容的补充,必须依附于主合同,而不能独立于主合同存在,那么,主合同所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也适用于补充协议。”[4]
在对赌协议纠纷中,一般认为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与涉及对赌内容的补充协议所对应的交易系属同一交易。即,投资方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或者受让标的公司股权,同时以标的公司净利润的业绩目标或上市目标的实现作为投资估值调整依据的一次股权投资。各方在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了整个交易结构、方式、步骤、条件等,各方对其中的权利义务是知悉、清楚的,并且在此后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无异议,而是依据合同约定的交易框架进行调整。[5] 司法实践中,法院亦是倾向于认为该等协议密不可分,如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在(2021)青民终74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案涉《合作协议》《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购买协议》及相应《股权回购协议》《股权质押合同》《担保合同》等补充协议,虽先后签订,但协议内容密切相关,应当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评价。”[6]
因此,对赌协议纠纷中,考虑到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主合同与涉及对赌内容的补充协议之间密不可分,若主合同约定了仲裁协议,补充合同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时,主合同的仲裁协议效力扩张适用于补充协议。
在涉及对赌的投资交易中,除签订补充合同的情形外,投资方与融资方可能会以签订担保合同、担保函等形式,为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服务,并与其构成主从合同关系。当该等从合同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时,是否受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主合同中仲裁协议的约束?
此前,有观点认为,若从合同无仲裁协议,主合同仲裁协议效力不能扩张适用于从合同。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成都优邦文具有限公司、王国建申请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2011)深仲裁字第601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13]民四他字第9号)中认为:“案涉担保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仲裁庭关于主合同有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7]如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京04民特32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本案中,EEI公司(原名称为EEIS.R.L)并未参加2011年3月9日当天《采购合同》的签订,其于2011年4月5日签署的合同附件七担保函,担保函中载明EEI公司为此合同的履行提供担保,与意利埃公司承担同样的责任。该担保函在EEI公司与万源公司之间形成担保法律关系。而对于该担保的争议解决方式,担保函中并未进行约定,同时相关法律亦无主合同约定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亦应适用仲裁的规定。因而在EEI公司与万源公司未就担保的争议解决方式达成仲裁合意的情况下,贸仲认为《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同样适用于该担保函的管辖处理意见,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8]
但是,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少认定主合同仲裁协议可以约束从合同的案例,法院从担保人身份和从合同内容的角度,认为担保人对主合同的签署及内容是明知的,进而认为担保合同即从合同亦受到主合同仲裁协议的约束。如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京04民特934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陆志明主张其与万安天成中心之间没有仲裁协议,实是主张《承诺担保函》不受《股权转让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束。对此,本院认为,从陆志明的迈迪金公司股东身份及《承诺担保函》中其承诺内容来看,其应当知道《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及内容,《承诺担保函》虽形式上独立,但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及《承诺担保函》的签署内容,《承诺担保函》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的组成部分,应受到《股权转让协议》的仲裁条款约束。陆志明主张其与万安天成中心之间没有仲裁协议,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9]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沪01民特483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庹小兰作为XX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员工,其对《债权转让及居间协议》的内容包括仲裁条款是明知的。该担保书系庹小兰对崔秀平的单方承诺,若发生争议,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而言,争议管辖依照法律规定应根据主合同即《债权转让及居间协议》确定案件的管辖。此外,本院还注意到,就本案庹小兰的担保责任,崔秀平曾向江苏海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院经审查后认为,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故应根据《债权转让及居间协议》确定管辖,即崔秀平应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该院作出(2020)苏1202民初2311号民事裁定,驳回崔秀平的起诉,该案现已生效。”[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或者担保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的,人民法院对约定仲裁条款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无管辖权。”然而,该条款并未明确在主合同存在仲裁条款,担保合同既未约定诉讼管辖条款也未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况下,担保合同是否受主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司法部于2021年7月30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仲裁法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四条规定:“纠纷涉及主从合同,主合同与从合同的仲裁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从合同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主合同的仲裁协议对从合同当事人有效。”根据该条款,对于从合同没有仲裁协议的,主合同的仲裁协议效力扩张适用于从合同。
目前,《仲裁法征求意见稿》还在征求过程中,对于上述第二十四条规定,有观点认为其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但是,考虑到从合同纠纷的处理势必涉及对主合同的审查乃至判断,从提升争议解决效率的角度,在从合同未另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将主合同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适用于从合同,具有相当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在对赌协议纠纷中,当投资方与融资方在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主合同中约定了仲裁协议,但在涉及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等对赌内容的补充合同中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时,考虑到上述主补合同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主合同的仲裁协议效力扩张适用于补充协议;当投资方与融资方在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主合同中约定了仲裁协议,但在为对赌义务提供担保的从合同中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时,虽然目前的司法实践观点不一,但是结合《仲裁法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考虑到主从合同的处理与审查,为了提升争议解决的效率,主合同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适用于从合同有可能是未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