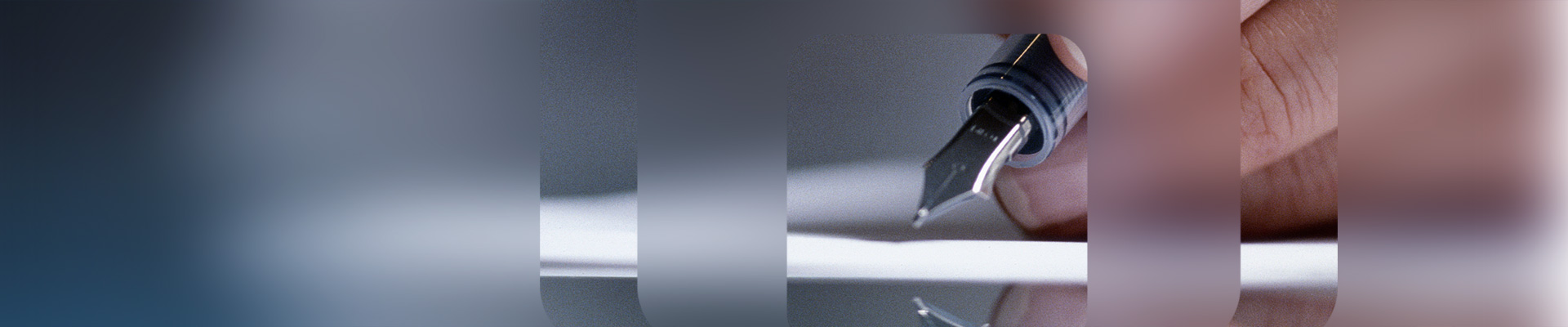关联担保中“关联”范围的司法实践研究
问题的提出
根据《公司法》第16条[1]、《九民纪要》第六部分 “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如第17、1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解释》”)第7条[2]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对外担保效力的认定审查的是相对人善意与否,目前对相对人善意的判定是看其对公司决议的审查,不谈其形式审查要达到何种程度,对决议的审查首先应区分是否为关联担保而分情况讨论[3],因为若为关联担保,则必须由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非关联担保则仅需由公司章程规定决议机关为董事会/股东(大)会。上述规定显然对关联担保提出了更高的决议审查要求,从相对人的角度而言,在有公司决议的情况下,因决议效力对担保效力产生争议的情形下,非关联担保证明责任更小,证明标准更低,更能保护自身权益,故关联担保的成立的问题涉及担保人与相对人的利益衡量问题,实践中分歧较大。
就关联担保之成立,如仅按《公司法》第16条第2款规定,限定为“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担保”,则若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利用其在公司内部享有的优势地位,令公司为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规避关联担保的认定,只需董事会决议即可,则可能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关联担保”之“关联”范围是否应为扩大解释,又如何作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议。
司法实践争议
(一)现行法律规范
对关联担保成立的分歧,主要集中于 “关联”这一要点的认定,现行《公司法》内部并不统一自洽,就其第16条第2款,关联担保限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担保”,而第216条第4项规定的关联关系则更为宽泛,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关联关系的界定尺度更有扩张,目前主流意见是以《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号)第4条为指引,根据交易所规则加以认定,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证发〔2023〕31号)第6.3.3条[4]。
因此,为解决实践中对于关联担保中“关联”要点的界定的争议,《九民纪要(征求意见稿)》曾意图增设“等与公司有关联关系的主体”的兜底性表述以扩张对关联担保的认定,从保护担保人中小股东权益的角度,抑制实际控制人通过其他关联主体刻意规避关联担保审议要求的现象。然而,在《九民纪要》正式稿中出于对相对人审查成本的担忧,仍顺延了《公司法》的安排。法律规定对关联担保进行了严格限缩;与之相反的是,从裁判实践中来看,对于关联担保的范围之扩张颇有跃跃欲试之态。
(二)裁判观点梳理
如上所述,现行法律明文认可的关联担保主体仅为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但即使是上述两类主体,裁判中也存在需予以考虑的特殊情形。
1.“股东”认定之特殊情形
对于公司股东为关联担保主体,实践中本无争议,但考虑到公司股权设计的复杂性,多有通过间接控股或隐名持股的情形,此时的认定就不应局限于文义,可能存有以下两种特殊情形:
一是“股东”为间接控股股东/隐名股东,如案例1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与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8)鲁民初74号】中,山东高院认为:“本案中技公司既是富控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又是宏达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富控公司、宏达公司为中技公司所提供的担保系关联担保,必须经其股东大会决议。”间接控股股东/隐名股东往往还多存在构成实际控制人问题,本文拟于下一部分对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做详解。
二是“股东”为实际借款人,即借款人名义上为股东亲属,实际上为公司股东的情形。如案例2 伍家鋐、廖荣纳企业借贷纠纷【(2020)最高法民申4620号】中,最高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在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就已了解廖莎、廖美娜不是实际借款人,各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并无异议,……案涉借款合同实际借款人为廖荣纳,伍家鋐对此是明知的。……廖荣纳是利菱公司股东,原审判决认定利菱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构成关联担保并无不当。”
2.实际控制人的认定问题
就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根据《公司法》第216条的定义,是指虽然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裁判观点同样对此予以回应,如案例3 瓮安县磷化有限责任公司、孙静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9)最高法民终887号】中,最高院对实际控制人的定义为:“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结合中盟公司通过美辰星公司间接持有磷化公司61%股权的事实,可以认定中盟公司系磷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实践中法院却多从股权结构出发判断实控地位,忽略了实际情况较为复杂,实际控制的手段是多样的可能性。
首先,就投资控制,实践中的认定难点集中于间接持股情形下的认定。如案例4 佛山市南海能顺油品燃料有限公司、杜敏洪买卖合同纠纷【(2019)最高法民终30号】中,最高院认为:“能顺公司股东为杜敏洪、杜觅洪。能顺公司原持有能盛公司90%股份,后经股权转让使何锦堂成为能盛公司一人股东,但该股权转让行为的证据不足采信。杜敏洪、杜觅洪作为能顺公司的股东,通过能盛公司的一人股东何锦棠构成对能盛公司的实际控制。”
其次,就协议控制方式也多样化,除通过一致行动人协议,如案例5 【(2019)湘01民终3799号】中,长沙中院认为:“同时王云平除直接持有蓝创公司股权外,还担任蓝创公司董事长,能对蓝创公司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并实际控制蓝创公司的经营决策,因此王云平与一致行动人(即郭征南)系蓝创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还可通过多协议协同控制,如案例6 金燕与建银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2018)京民终18号】中,北京高院认为:“小马奔腾集团公司搭建VIE架构后,湖南优化公司通过协议控制境内多家公司,李萍、李莉在境内的股权都质押给了湖南优化公司,表决权也委托湖南优化公司行使,而湖南优化公司的董事及最终受益人都是李明和金燕。证明当时表面上李萍、李莉是小马奔腾的股东,实际上小马奔腾是李明和金燕二人通过湖南优化公司实际控制。”
最后,其他安排控制则更为复杂多变,目前司法裁判已经认定的方式有隐名代持[5]、特殊身份关系控制[6]、控制公司证章照及核心经营资料[7]等方式,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核心在于其控制权,可“控制公司董监高等人事的任免”、“对公司的重大事项具有决策权”等。如案例7 梁烜荣、梁伟娜等买卖合同纠纷【(2021)最高法民申4488号】中,最高院认为:“梁烜荣虽非力天公司的股东,也非董事,且不担任任何职务,但其系力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发起人,并具有力天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的实际委任权。因此,梁烜荣为泰裕公司实际控制人。”
关联担保范围的扩张解释
上文已对现在裁判中关联担保中“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作了细致的梳理,实务中争议最大的其实是尚未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如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提供担保是否构成关联担保,下面我们对这一问题结合司法裁判作分析。笔者认为,审判的核心还是立足于《公司法》第16条的立法目的,即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一)裁判争议
1.否定说
实践中不乏有法院对此类扩张不予认可的情形,否定观点基本都立足于文义解释,如案例8 上海尤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上海夏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0)沪民终599号】中,上海高院认为:“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实际控制人”扩张解释为包括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关联人,已超出法律条文通常的文义范围。”又如案例9 北京思瑞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莱州环日置业有限公司等保证合同纠纷【(2020)鲁民终2277号】一案中,山东高院认为:“关联担保仅限定于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担保,并不包括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投资的其他关联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
2.肯定说
而肯定观点则多从实质内容进行审查,如案例10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南华深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赖淦锋其他合同纠纷【(2020)沪74民终289号】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董事会具有相当影响力,如果该担保仅需董事会决议即可通过,恐无法体现公司决策的集体意志,容易使中小股东利益受损。因此,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立法目的和精神,应认定天润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赖淦锋所控制的另一家公司提供担保亦属法律规定的“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须经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关联担保之情形。
又如案例11 江苏理文造纸有限公司与江西粤东纸业包装有限公司、高邑县粤东纸业包装有限公司等定作合同纠纷【(2020)苏民申5163号】中,江苏高院认为:“公司为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公司提供担保,属公司控股股东与其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关联交易的情形,该担保行为实质由控股股东获利,该后果与公司直接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并无本质不同。因此,股东与债务人利益高度重合的情况下,已构成股东利用公司担保输送利益,若不适用《公司法》十六条第二款,将使得该条款立法目的落空。因此该担保实质上应视为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
此外,若公司章程已对关联担保范围有规定,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也当然构成关联担保,如案例12 山东华盛农业药械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新丝路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2020)最高法民申6387号】中,最高院认为,“本案中,钱春生既是新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又是新丝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新光公司系新丝路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关联方。依据前述规定,新丝路公司为新光公司向华盛公司提供反担保,应由新丝路公司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裁判审查要点
对上述持肯定观点的支持案例进行分析,可发现其立足点都是为了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此与《公司法》第16条的立法原意相契合,正如最高院在经典案例——案例13 强静延、曹务波股权转让纠纷【(2016)最高法民再128号】的再审判决中所言:“《公司法》十六条之立法目的,系防止公司大股东滥用控制地位,出于个人需要、为其个人债务而由公司提供担保,从而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权益。”
虽然近些年的司法裁判观点多有冲突与争议,但此要点现在仍可认为是现行的裁判方向,典型体现即为最高法院公布的“全国法院系统2022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获奖名单”中一等奖获奖案例——案例14 重庆璟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鸿盛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2022)渝05民终5682号】,此案的裁判要旨可概括为:非上市公司为其实际控制、间接持股100%的公司提供担保无需决议。
在此案中,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担保人公司实际控制被担保人公司100%股权的情形中,虽然担保人公司通过了多层股权架构持股,但在任何一层股权架构中,均不存在其他股东利益,也即是担保人公司为其实际控制、间接持有100%股权的公司提供担保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样不存在为其他股东输送利益的情形。此种情形下,即使公司对外担保未经公司决议,也不违背《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之法目的和《担保制度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范目的,不能因此认定该担保不对公司发生效力。”
可见,要求相对人对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效力进行形式审查,主要是从保护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角度考量,如本文开篇所述,避免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利用内部优势损害公司自决。因此,即使构成关联担保,若因实际控制人100%控股,不存在对其他股东利益的贬损,同时此种担保确实是实际控制人出于利己的目的指示担保人提供担保的,根本无必要决议;此种裁判方向也可以避免对关联担保的机械认定,以免担保公司利用此理由逃避担保责任的承担,事实上,实务中对担保协议的效力提出质疑也往往是提供担保决议的担保人。
如案例1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北新支行、奥瑞德光电(东莞)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0)最高法民终180号】中,担保人即以案涉公司担保决议仅有法人股东之签章而无自然人股东签名的事实,进行决议无效之抗辩。在此案中,担保人有一法人股东人和另一自然人股东,然自然人股东因未实缴出资而不享有表决权,法人股东为该公司唯一享有表决权的股东,公司的决策经营管理权均由其行使,并无适用《公司法》第16条第3款的前提条件。因此对该决议效力最高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禁止关联担保,而是通过公司内部治理的特别决议机制来确保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防止公司大股东利用关联担保损害公司或者小股东利益。而本案中东莞奥瑞德公司唯一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提供担保,不仅体现股东意志,也体现公司意志,不能依据该条款的规定认定仅有股东哈尔滨奥瑞德公司签章的公司决议非东莞奥瑞德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张宏未在《关于承担经济担保事项的决议及授权书》签字,认定东莞奥瑞德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可见,裁判观点对关联担保之“关联”范围的扩张,审查点在于是否体现公司意志,是否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中小股东利益。在有权参与表决的同意公司提供担保的股东为100%控股的情形下,甚至不需要决议的存在,同样审查路径的还如案例16 汇信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江门创彩科技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2021)粤03民终35086号】中,在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时,公司股东除去该被担保人,另一位同意提供担保的股东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了公司剩余81.6%的股份,在此情况下,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未对关联关系进行审查,就直接认可了决议的效力进而认可了担保协议的效力。
(三)相对人就“关联”关系的审查义务
《九民纪要》第18条虽确定了如何审查相对人之善意,但其区分关联担保的构成与否是从客观角度入手,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在客观情形与相对人主观认识不一致的情形下,此种设定加重了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即相对人未能识别出案涉担保性质而其又在客观上构成关联担保时,相对人将处于不利地位。结合对下列案例的分析,我们认为,在担保人非为上市公司的情形下,相对人就“关联”关系的审查义务除公司章程外,还需考虑对担保人工商信息的查阅。
在现今股权设计多样化、复杂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如上所列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手段还需兜底条款覆盖认定的情形,实践中不乏 关联担保中“关联”关系较为隐蔽的情况,此时相对人利用外部信息难以获知或者识别担保中的关联关系,更无法认识到案涉担保关联担保,此时若再以关联担保之决议标准要求相对人,未免有不当加重相对人审查义务之嫌。即使是相对公开的股权结构,有时也难于发现实际控制关系,如上述案例12,股东在通过境外公司间接持股担保人时,境外持股材料在境内工商登记信息中并未显示,此时裁判观点为由于案涉担保人属新三板公司,因此其实控关系曾在股转系统当中披露,因此可推定相对人知悉该等关系存在。在债权人明知实际控制关系时,成立关联担保。
为解决此问题,《担保解释》放弃了九民纪要的明确分类模式,而是引入了概括性的善意标准。将相对人对关联担保构成本身的审查纳入到“善意”的讨论范畴,从而能够实现更为合理的成本分配。但此概括标准难为关联担保识别提供必要指引,实践操作仍须结合案例进行类型化处理。
对于“关联”关系的认定,现有法律条文明确提出的仅有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但在“关联”关系的审查也构成对“善意”的认定,则至少就实际控制人之认定,公司章程难有完整体现,在此情形下,将工商登记信息纳入“合理审查”范围,乃应然之理。从裁判观点中可知,工商信息的核实确属部分法院审查相对人善意之要点。如案例17 山东章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章丘某某机械有限公司、侯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0)鲁0181民初4929号】中,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认为:“华威公司于2017年10月29日同意为某某公司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亦无华威公司当时工商登记股东侯某某、陈某某签名,章丘农商行对华威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未进行形式审查而与之签订保证合同,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系非善意相对方”。
公司为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系常见而特殊的一类“非典型”关联担保,通过前述判例梳理可以发现,该类担保实际上是“间接使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受益,同时又可能有损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在订立担保合同伊始,通过公开途径并不难识别这种特殊的关联担保。因此,在订立合同时需对决议审查予以特别的关注,否则在后续的担保行为效力审查中,将存在被法院判定为无效的风险,从而难以要求担保人承担全部担保责任。
结语
(一)总结
现有法律规定虽仅承认了为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担保为关联担保,但在间接持股股东、隐名股东及股东为实际债务人的情形下,关联担保的认定已经不仅限于文义,实践中对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更是纷繁复杂,故尽管存在分歧,司法裁判总体方向上并未局限于严格的文义解释,立足于保护公司自决进而保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角度,适当将关联担保范围扩张至“为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提供的担保”自然也为应有之义。关联担保认定范围的扩张也对相对人的审查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建议
从提供担保的公司及股东角度而言,在关联担保范围可否作扩大解释仍有争议的实践背景下,为维护公司利益,限制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的不当决议(担保)行为,应在章程中对需股东大会决议的关联担保范围作适当扩张,以便后续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从相对人角度来说,应提高对自身审查义务的标准,以尽力达成“善意”相对人之认定,区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并尽可能作好“关联”关系的审查,将对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纳入审查范围可对“善意”要件之证成提供有利依据,以尽可能争取自身有利的诉讼地位,尽量避免对方借故抗辩,逃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