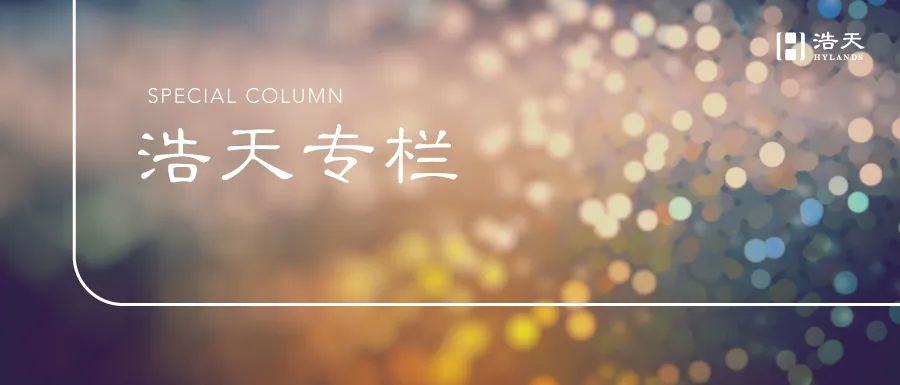国际建工项目:即便无修复缺陷的意图,业主仍可主张补救成本
如果承包商存在施工缺陷,业主可以寻求以“补救成本(cost of cure)”作为损害赔偿。但若是业主其实并不打算修复这些缺陷,是否仍有权获得以“补救成本”形式体现的损害赔偿呢?换句话说,业主修复缺陷的意图对于是否应判给“补救成本”作为损害赔偿这一问题是否相关呢?对这个问题,在Terrenus Energy SL2 Pte Ltd v Attika Interior + MEP Pte Ltd and another case [2025] SGHC(A) 4案中,新加坡上诉法院就相关的法律原则进行了分析。
案例背景
2021年4月5日,双方就新加坡樟宜商业园的一个太阳能发电设施的建设签订了总承包商协议(Main Builder Agreement,以下简称"MBA")。Terrenus聘请Attika作为该项目的总承包商。合同总价为510万美元。
就本次上诉而言,MBA中的以下条款至关重要:
(a) 附件A规定了Attika的工作范围。这包括项目的安装、测试和调试。Terrenus负责提供太阳能电池板以及两个电网变电站的供应和安装等工作。
(b) 附件F——题为“付款时间表”,规定合同总价分三个里程碑支付:(a) 根据每月各子项的进度支付40%;(b) 在新加坡建设局(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颁发临时占用许可证(Temporary Occupation Permit)时支付20%;(c) 在新加坡建设局颁发法定完工证书(Certificate of Statutory Completion)时支付40%。
(c) 第5.5条规定了工程完工的各个日期。根据第5.5.1条,Attika有义务在“完工日期(Date of Completion)”前尽快完成工程,该日期在MBA附录中规定为2021年7月31日。根据第5.6.1条,Attika还有义务满足“部分完工(Partial Completion)”的要求,第1.3.12条将其定义为“在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早于完工日期),完成部分工程以便至少使樟宜商业园的70%能够通电并投入使用”。第5.5.5条、5.5.6条和5.5.7条规定Attika可正式申请工期延长(“EOT”),Terrenus可选择接受或拒绝此类申请。
(d) 第14.3条规定Terrenus可在Attika无违约的情况下终止MBA。在此情况下,Terrenus必须按照第14.3.2条的规定,向Attika支付“截至终止日期按[MBA]规定已完成的所有工程的款项”。
2022年1月12日,新加坡建设局颁发了该项目的临时占用许可证。
2022年2月3日,Terrenus依据MBA第14.3条在Attika无违约的情况下终止了与Attika的合作。
2023年7月6日获得National Parks Board关于颁发法定完工证书的批准,并于2023年7月13日颁发了法定完工证书。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Terrenus未能支付部分款项,导致双方依据2004年《建筑业付款保障条例》(2020年修订版)(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Security of Payment Act 2004 (2020 Rev Ed))进行了几轮审裁程序。
随后,Terrenus提起诉讼。它提出了多项请求。其主要请求是因工程缺陷导致的损害赔偿。具体而言,Terrenus声称Attika未能确保太阳能电池板安装结构杆(以下简称"PEG杆")按照MBA的规定埋入地下至少500毫米深。Terrenus认为,由于未能达到合同规定的最低埋深,导致在强风天气下太阳能电池板有结构故障的风险,因此有权要求赔偿PEG杆的整改费用。Attika则辩称,Terrenus既未能证明不符合规定的程度(extent of non-compliance),也未能证明因这种不符合在强风天气下会导致结构故障的风险。
一审法院做出如下判决:
Terrenus未能证明Attika所施工的工程存在重大缺陷。关于PEG杆埋深问题,尽管Terrenus已证明部分PEG杆未达到规定埋深,但它未能举证证明(1)不符合的程度,以及(2)因这种不符合而在强风天气下导致结构故障的风险。因此,Terrenus仅获得1500美元的名义损害赔偿(nominal damages)。
Terrenus提起上诉,其中的一个关键抗辩是:
法院应就Attika未将PEG杆安装到合同规定的最低深度,判给Terrenus实质性损害赔偿。Terrenus公司已就不符合规定的程度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其提供的专家证据可靠。此外,法官错误地认为Terrenus公司必须任何偏离合同最低深度的情况会造成结构风险,才能获得实质性损害赔偿。但这种不符合规定的情况本身就是一种违约行为,基于补救成本,Terrenus公司就有权获得损害赔偿。
争议焦点
Terrenus是否有权因Attika未将PEG杆嵌入到合同规定的最低深度而获得实质性损害赔偿?
法院判决
新加坡上诉法院指出,就本案案情来讲,Terrenus的主张能否获得支持取决于两个要点。其一,Terrenus是否完成了举证责任,证明不符合规定的PEG杆的数量和程度;其二,Terrenus是否有权要求以补救成本作为损害赔偿。
关于Terrenus是否完成了举证责任,以证明不符合规定的PEG杆的数量和程度的问题,上诉法院认同一审法院的看法,认为Terrenus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Terrenus提供的专家证据仅仅是其单方任命的专家单独进行的检查报告,而非双方专家的联合检查报告。除此之外,这些检查报告也无助于证明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其中包含的847张PEG杆的照片并未与现场所谓不符合规定的PEG杆相对应;事实上,其中一些照片拍摄的是符合规定的PEG杆。
由于Terrenus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其要求以补救成本作为损害赔偿的主张不成立。不过,上诉法院还是考虑了第二个要点,即假设不符合规定的情况成立,补救成本是否可得到支持。
Terrenus辩称,除非Attika能证明补救成本过高,否则其有权要求以补救成本作为损害赔偿。如果PEG杆未安装到规定深度,Attika将违反MBA合同,Terrenus有权要求以补救成本作为损害赔偿。补救成本是合理的,因为强风可能会造成结构风险。Terrenus正试图消除新加坡最大的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电站之一的结构不稳定风险,并且仅针对被认定为存在结构风险的区域。
Attika则辩称,不存在真正的结构故障风险,因此授予补救成本完全不合理。此外,Attika指出,Terrenus并无修复所谓不符合之处的意图。Attika认为,既然没有修复的意图,就不应下令支付补救成本。
新加坡上诉法院指出,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存在相互冲突的观点。一方面,由于违约损害赔偿的首要考量是将受害方置于如同合同已被履行的状态(put the claimant in a position as if the contract has been performed),法院通常并不关心受害方打算如何使用所判给的损害赔偿。另一方面,如果受害方无意实施修复措施,那么在直觉上人们不愿判给“补救成本(cost of cure)”。关于索赔方进行修复的意图与授予补救成本的关联性及关联程度的问题,法律并没有统一且明确的定论(见Edwin Peel, Treitel on The Law of Contract (Sweet & Maxwell, 15th Ed, 2020) at para 20-046)。当前的上诉案件提供了一个阐明该问题的机会。
在新加坡高等法院最近作出的JSD Corporation Pte Ltd v Tri-Line Express Pte Ltd [2023] 3 SLR 1445(简称“JSD Corp案”)判决中,法院认为,在评估授予补救成本的合理性时,修复意图是一个重要因素,若无非常特殊的抵消因素,未能证明有修复意图将导致补救成本的索赔不被允许(见JSD Corp at [82])。
但是,上诉法院并不同意JSD Corp案中所表达的观点。修复意图既不是授予补救成本作为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prerequisite),通常也不具有JSD Corp案中所赋予的重要分量。上诉法院认为,修复意图只是在评估授予补救成本作为损害赔偿是否合理且适度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下面是上诉法院给出的详细说明。
(1) 权威判例
在早期英国有两个案例似乎认为,索赔方实施补救工作的意图是判给补救成本的先决条件。在Tito v Waddell (No 2) [1977] Ch 106案(“Tito案”)中,被告在将原矿场归还给原告时,未能在一座岛上重新种植树木和灌木丛。原告无意进行重新种植。Megarry大法官指出:“如果原告……无意将任何损害赔偿用于履行合同约定的工程或其等效工程,我看不出他为何应该获得用于开展永远不会进行的工程的花费”。因此,未判给补救成本。
在Radford v De Froberville [1977] 1 WLR 1262案(“Radford案”)中,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未能建造一堵墙。Oliver法官认为,原告能否索赔代表建造一堵墙成本的损害赔偿,取决于原告“是否有真正且严肃的意图去实施该工程”。由于原告有意这么做以保护其土地的隐私性,因此判给了补救成本。
在Ruxley Electronics and Construction Ltd v Forsyth [1996] AC 344案(“Ruxley案”)中,上议院认可了Tito案和Radford案的判决。然而,Ruxley案似乎认为这种意图只是确定判给补救成本是否合理的一个因素。Jauncey大法官和Lloyd大法官都解释说,法院并不关心原告如何使用损害赔偿款。但在他们看来,修复意图在表明寻求补救成本的合理性方面可能是相关的,因为它能证明实际遭受的损失程度以及索赔方真正想要进行补救的诚意。
此外,在Linden Gardens Trust Ltd v Lenesta Sludge Disposals Ltd [1994] 1 AC 85案(“Linden Gardens案”)中,Griffiths大法官似乎也重视当事人补救违约的意图。他指出,在判给损害赔偿时,“法院当然希望确信修缮工作已经或很可能得以实施”。在Alfred McAlpine Construction Ltd v Panatown Ltd [2001] 1 AC 518案(“Panatown案”)中,上议院多数法官也认可修复意图对于判给补救成本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Panatown案的反对意见中,Goff大法官和Millett大法官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未收到合同约定的履行本身就构成了当事人的损失,无需当事人发生或意图发生补救成本。因此,仅违约这一事实就足以让当事人索赔实质性损害赔偿,而不论其是否已发生或意图发生补救成本。
在一些案例中也赋予修复意图更高的权重,认为修复意图是法院决定是否判给补救成本的关键因素:参见St James’s Oncology SPC Ltd v Lendlease Construction (Europe) Ltd & Ors [2022] EWHC 2504 (TCC)案(“St James’s Oncology案”),以及London Fire and Emergency Planning Authority v Halcrow Gilbert Associates Ltd [2007] EWHC 2546案(“London Fire案”)。因此,英国在这方面的立场并不明确。
澳大利亚的立场则更为明确。在涉及建筑质量缺陷的案件中,修复意图在决定是否判给补救成本时通常不太相关:参见Bellgrove v Eldridge [1954] HCA 36案,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该案中认为当事人修复不稳定房屋的意图对于是否应判给补救成本这一问题“无关紧要”。De Cesare v Deluxe Motors Pty Ltd (1966) 67 SASR 28案(“De Cesare案”)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式,南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指出:“有时业主的意图对于某一行动方案的合理性可能是相关的……但另一方面,当建筑工程明显存在缺陷时,在我看来,业主没有修复缺陷工程的意图,并不能支持也无法得出判给补救缺陷工程的成本是不合理的这一结论”。同一法院在Unique Building Property Ltd v Brown [2010] SASC 106案(“Unique Building案”)第[94]段中还指出:
这并不需要考虑被告未来是否有继续按照合同进行建设的意图,甚至是否打算出售该地块。如果使工程符合合同的唯一合理方式是通过拆除重建,因为单纯的整改和修理不足以使工程符合合同要求,并且这种方式是合理的,那么拆除重建就应作为损害赔偿的衡量标准。至于业主实际上如何处置因任何法院判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款,则由其自行决定。
显然,澳大利亚的立场与Ruxley案中Jauncey大法官和Lloyd大法官的观点基本一致,即修复意图最多只是决定是否判给补救成本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在新加坡,涉及这一问题的案例始于MCST Plan No 1166 v Chubb Singapore Pte Ltd [1999] 2 SLR(R)1035案(“Chubb案”)。Chubb案涉及在一个公寓安装的有故障的安全与通讯系统。法院认为,判给补救成本是不合理的,“因为不清楚原告是否会花费这笔金额并开展这样一个更换项目”。这一问题也在涉及第三方利益的合同案例中得到了探讨。在Chia Kok Leong v Prosperland Pte Ltd [2005] 2 SLR(R) 484案(“Chia Kok Leong案”)中,法院认为受诺人修复的意图并非请求补救成本的先决条件。
JSD Corp案指出了Chubb案和Chia Kok Leong案在这一问题上得出的不同结论,并更倾向于Chubb案所表达的立场。JSD Corp案进一步阐述了Chubb案的立场在原则上为何合理。虽然原告对损害赔偿款的使用方式通常并不重要,但这仅适用于原告已经遭受损失的情况,比如已经支付了补救成本的情形。如果尚未发生损失也没有发生补救成本的意图,那就还不是实际损失,此时原告仅有价值减损(diminution in value)和任何间接损失(consequential loss)的请求权。因此,原告未来是否有意图使用所判损害赔偿款来支付补救成本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没有这种意图,原告就并未遭受补救成本这一损失。
JSD Corp案还指出,从政策角度来看,考虑修复意图可确保原告不会获得超过其损失的赔偿。另一方面,反对观点认为,考虑修复意图违背了法院不关心原告如何花费损害赔偿款的原则。法院驳回了这一反对观点,认为其不合理,因为它忽略了更根本的事实,即损失尚未确定。
JSD Corp案承认,这一分析表明修复意图应作为判给补救成本作为损害赔偿的先决条件(prerequisite),而非仅仅是一个考虑因素。然而,出于对现有判例(主要是Ruxley案以及随后的The Maersk Colombo [2001] 2 Lloyd’s Rep 275案的尊重,JSD Corp案的法院将其结论限定为修复意图是评估判给补救成本作为损害赔偿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在缺乏非常特殊的抵消因素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补救意图,原告关于补救成本损害赔偿的请求将被驳回。
(2) 上诉法院的分析
在对过往的权威判例中的观点进行整理后,上诉法院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上诉法院先从违约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说起。众所周知,违约损害赔偿的目的是在金钱所能及的范围内,使受害方处于如同合同得到履行时的相同状况。简而言之,受害方应就其期待利益损失(expectation loss)获得赔偿,即实际收到的与合同所承诺内容之间的差距。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违约损害赔偿方式,如信赖利益损失赔偿(damages for reliance loss)或恢复原状赔偿(restitutionary damages)。然而,这些赔偿类型仅在有限的情形下适用,并且从属于期待利益损失赔偿,后者是合同违约的主要和默认救济方式。
弥补期待利益损失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所交付产品的价值减损(diminution in value)。这种方法旨在尽可能使受害方处于如果合同得到履行时本应有的财务状况(financial position)。其二,补救成本(cost of cure)。此方法旨在使受害方处于如果合同得到履行时实际应有的状况(actual position),目的是给予受害方获得实际履行的经济手段(financial means to obtain actual performance)。在这方面,补救成本衡量的是获得实际履行的手段,而非期待利益损失。
根据“契约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原则上受害方始终有权要求合同得到实际履行。实现这一目标的直接方式是通过衡平法上的实际履行(specific performance)救济措施。然而,出于实际、政策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法院不愿强制一方履行其合同义务,实际履行救济被认为具有特殊和非同寻常的性质。而在补救成本赔偿方面,并不存在强制合同一方履行义务所引发的那些担忧。从某种意义上说,补救成本是弥补受害方期待利益损失最合乎逻辑且直接的方法,因为它最接近于在不强制违约方履行的情况下给予受害方实际履行的结果。
因此,在涉及有缺陷的建筑时,早期案例通常将补救成本视为正常的损害赔偿衡量标准:参见McGregor on Damages (Sweet & Maxwell, 21st Ed, 2021) at para 31-012,其中引用了Thornton v Place (1832) 1 Moo. & Rob 218案、Dakin v Lee [1916] 1 KBB 566 CA案、East Ham Corp v Bernard Sunley [1966] AC 406案以及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 Norman & Dawbarn (1986) 2 Constr LJ 280案。
然而,合理性(reasonableness)和比例性(proportionality)考量以授予补救成本作为损害赔偿的一种务实限制因素发挥作用。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在某些情况下,补救成本的数额可能与期待利益损失的价值不成比例,以至于即使受害方原则上有权通过补救成本获得实际履行,但从实际或经济角度来看,授予补救成本并不合理。例如,在一栋建筑中,为了更换已建入结构中的不符合规定的组件,需要对建筑进行大规模拆除。当补救成本高于整栋建筑的价值,或者更换这些组件不会给受害方带来任何实际(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有益结果时,授予补救成本就不合理或不成比例:参见Jacob & Youngs v Kent 129 N.E. 889 (1921)案,Morris v Redland Bricks Ltd [1970] AC 652案,以及James v Hutton [1950] 1 KB 9案。
当法院评估授予补救成本的合理性或比例性时,实施补救成本的意图才具有相关性。然而,这只是评估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需要明确的是,它并非授予补救成本的先决条件(prerequisite)。这遵循了既定原则,即法院不关心胜诉的受害方如何使用所判定的损害赔偿款。
还有其他多个相关因素。在此不一一列举,一些例子包括:(a)补救成本与受诺人将获得的利益之间不成比例的程度(Ruxley案第353、367和369段);(b)损害或缺陷的程度及严重性及其后果(Ruxley案第357–358段);(c)合同的性质和目的,以及合同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已基本实现(Ruxley案第358段);以及(d)合同所承诺内容对受害方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Ruxley案第360段)。
许多认为修复意图至关重要的案例,通过简单应用合理性评估或许可以得到解释。例如,在Radford案中,批准建造遗漏墙体的成本是合理的——受诺人希望建造这堵墙以保护其土地的隐私,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式能让他获得合同约定的履行。同样,在St James’s Oncology案中,无论原告是否有修复意图,对于未符合消防安全标准的电气和机械中心进行修复都是合理的。相比之下,在Tito案中,鉴于原告重新种植岛上树木和灌木丛的成本与被告未履行义务所造成的期待利益损失的价值不成比例,无论原告是否有修复意图,判给原告这笔高额的重新种植成本都是不合理的。在JSD Corp案中,由于修复古董汽车的成本远远超过了价值减损,因此判给修复古董汽车的成本是不合理的。
众所周知,因合同违约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均在违约发生时即已产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应判给何种衡量标准的损害赔偿。这取决于哪种方式是依据合理性和比例性原则来解决受害人损失更为公平的方法。不应将是否遭受损失以及判给补救成本是否合理且比例适当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看起来JSD Corp案将损失的存在与损失的量化混淆了。
(3) 对本案事实的适用
尽管Terrenus就PEG杆的安装缺陷请求补救成本,金额为388,566.72美元,但很明显Terrenus无意修复所谓的缺陷。尽管声称担心安装缺陷带来的结构风险,但Terrenus在工程于2021年完工后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当被问及Terrenus是否无论上诉结果如何都打算进行补救时,Terrenus无法确认会这样做。此外,在不存在结构风险且无意进行补救的情况下,判给补救成本既不合理也不成比例。由于Terrenus未提供有关价值减损(diminution in value)的证据,法官仅就PEG杆问题判给名义损害赔偿是正确的。
Terrenus辩称,为了有权获得补救成本,并不需要证明存在结构风险——只要约定的履行没有完成就足够了。上诉法院不同意这一观点。Terrenus主张就PEG杆判给补救成本的理由中,主要因素就是太阳能电池板可能会被风吹走或损坏的结构风险。在不存在任何结构风险的情况下,[我们]不清楚与合同规定的嵌入深度仅有极小偏差这一点如何能证明应判给补救成本,尤其是考虑到索赔金额高达388,566.72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判给补救成本既不合理也不成比例。而且,Terrenus也并非主张在实际履行约定嵌入深度方面存在任何主观价值——毕竟这是一个商业性的太阳能电池板农场。
案例启示
缺陷是工程项目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而对于新能源项目来讲,快速的技术迭代使得缺陷变得更为复杂,修复成本也更高。因此,业主并不总是会选择修复缺陷。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若是业主根本没有修复缺陷的意图,是否可以请求补救成本作为损害赔偿?
新加坡上诉法院在本案中的分析表明,原则上只要合理且比例适当,一方当事人即使无意实际进行修复工作,也可以请求补救成本。尽管本案在这方面属于附带意见(obiter),但该判决仍然为新加坡的Chia Kok Leong案提供了支持,使新加坡与其他普通法管辖区(包括澳大利亚,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英国,不过上诉法院在本案中指出英国的立场尚不明确)更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