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绘画著作权相关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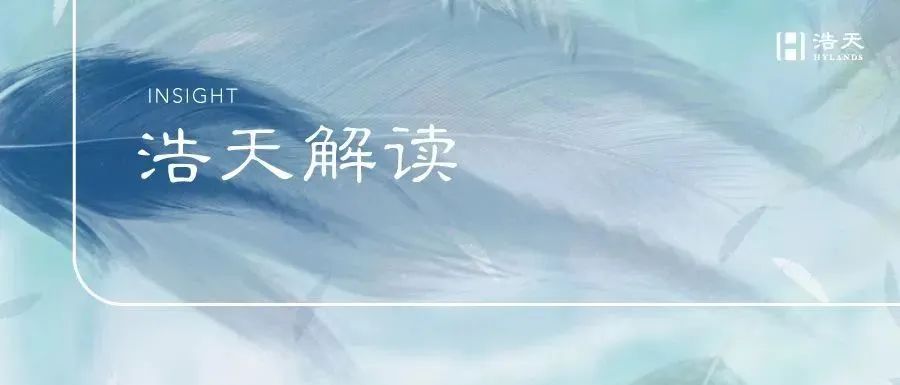
2023年2月21日,美国版权局为漫画家Kashtanova女士的漫画作品《Zarya of the Dawn》中由其本人创作的部分授予一定的著作权,并认为“Kashtanova女士是本作品文本以及写作及视觉要素的选择、协调和排布的作者。这部分作者权利受著作权保护”,但同时撤销了对该漫画作品中由AI技术生成部分的版权保护。新闻报道说:这是AI版权认证史上的里程碑。
另据报道:我国AI艺术家汪梓欣于2022年6月对画作《春江花月夜》在上海版权局申请版权登记,并于8月收到了该画作的数字版权证书。但其后,汪先生再就其他AI画作向上海版权局申请AI艺术作品版权登记时,均被退回,并被相关部门告知尚无AI艺术版权的明确规定,暂不接受AI艺术作品的版权登记。事实上,早在2018年,AI绘画《埃德蒙·德·贝拉米画像》(Edmond de Belam)在佳士得拍卖会上以43.25万美元成交。2022年12月8日,百度AI续画陆小曼未尽稿产生山水画《未完•待续》以110万高价在朵云轩拍卖30周年庆典上成交。2022年也被称为“AI绘画元年”,AI艺术平台迅速崛起,AI艺术作品涌现全网。据说,在主流平台上,只要输入简单关键词(例如:油画/水彩画等任一风格、构图、色彩、修饰词等)等待几十秒即可生成得到相应的画作。AI绘画彻底完成了从画师圈到普通民众的破圈。与民众高涨的热情截然相反,AI绘画也引发了艺术家的不满和抗议,认为AI绘画存在侵权风险、降低了艺术门槛、严重打击艺术家创作积极性、挤压了艺术家/画师的生存空间等等,进而发展为抵制AI绘画,画师社交平台涂鸦王国即公开声明拒绝AI绘画。此外,亦有针对AI绘画扰乱艺术品市场、阻碍艺术发展,乃至于存在被犯罪分子不法利用的担忧。有关AI绘画的各种争议始终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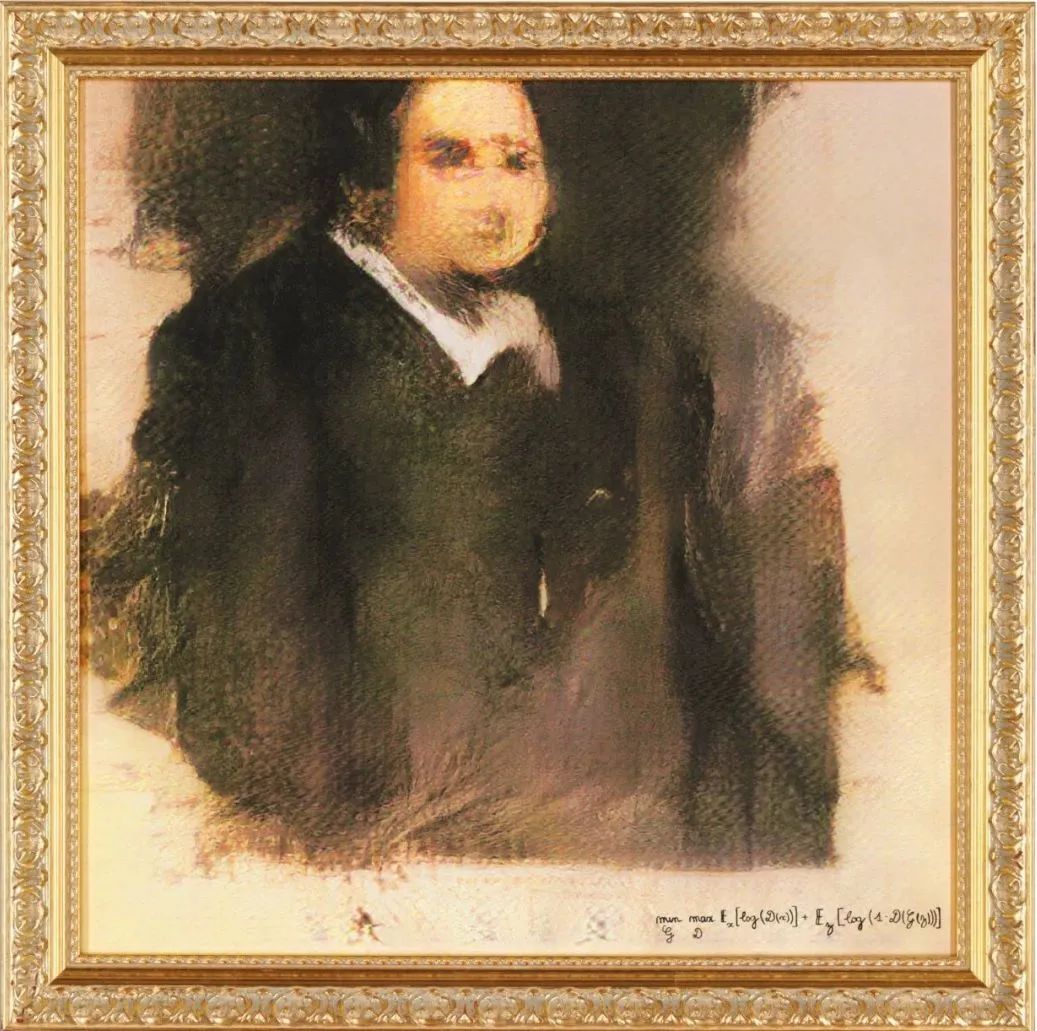

文心一格续画
《夏日山居图》
《埃德蒙·德·贝拉米》
作为法律工作者,笔者结合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工作实务等进行初步思考如下:
一、AI绘画具有可版权性的前提条件
在对于AI绘画是否具有可版权性的讨论中,很多讨论者喜欢引用美国更早的黑冠狝猴Naruto自拍照版权争议。该案件中,美国第九巡回法庭同样认为版权法保护的是人类智力成果,因此猴子不能成为权利人。按照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著作权人只包括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AI不是民事主体,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也不能成为著作权人。
是否保护以及如何保护AI绘画成果,司法实践目前尚无统一意见。学术界针对AI绘画保护手段有不同观点,比如,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针对AIGC采取类似“法人作品”进行保护;或者将AIGC视为是民法意义上自然人的“孳息”,由输入指令的自然人享有该“物”的孳息[1];或者增设邻接权[2];或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等等。
根据我国著作权相关法律,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根据上述规定,AI绘画是否获得著作权保护,主要在于其是否符合“独创性智力成果”特征。现行法律并未对“独创性”作出明确规定。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独创性也称原创作或初创作,是指一部作品是经作者独立创作产生的,是作者独立构思的产物,而不是对已有作品的抄袭。判断作品是否有独创性,应看作者是否付出了创造性劳动。作品的独创性并不要求作品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即作品的独创性与作品的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大小无关。作品的独创性也不要求作品必须是首创的、前所未有的,即使该作品与已有作品相似,只要该作品是作者独立创作产生的,也具备独创性。” 据此,考虑作者应当是民事主体的要求,由民事主体“独立构思、独立创作”,则具有独创性。
二、对AIGC中民事主体独创性的判断
如前所述,在AI绘画可版权性讨论中,持相反意见的观点认为“AI绘画不仅要满足独创性要求,还要是人类的智力成果”。也就是说:根据现行著作权法,作品应由自然人创作完成。即使满足“独创性”要求,但若不满足“人类智力成果”要求,也不能成为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这可能也是目前AI绘画在国内难以完成版权登记的主要原因。
在讨论AI绘画是否体现了人类智力成果也即民事主体独创性时,我们先参考国内以下两个案例:
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年5月18日(2019)京73民终2030号二审判决书(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VS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二审案)。
法院在该判决书中指出:涉案文章中的图形部分是菲林律师事务所基于收集的数据,利用相关软件制作完成,虽然会因数据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形状,但图形形状的不同是基于数据差异产生,而非基于创作产生。正如一审勘验过程中,一审法院将涉案文章中的图形与威科先行库生成的大数据报告1、2的相关图形进行对比,虽然涉案文章中的一些图形和大数据报告1、2的图形在图形数据、图形类别上存在不同之处。但是,该差异是不同的数据选择、软件选择或图形类别选择所致,所用图形均为数据分析常见的柱状图、饼状图、曲线图,不能体现菲林律师事务所的独创性表达。菲林律师事务所虽然主张对上述图形的线条、颜色进行了人工美化,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涉案文章中的图形不构成图形作品。
2.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4日(2019)粤0305民初14010号一审判决书(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VS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笔者注:网络检索未发现该案二审信息】
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在该判决书中指出:“涉案文章是由原告利用Dreamwriter软件在股市结束的2分钟内完成写作并发表。…涉案文章的生成过程主要经历数据服务、触发和写作、智能校验和智能分发四个环节。在上述环节中,数据类型的输入与数据格式的处理、触发条件的设定、文章框架模板的选择和语料的设定、智能校验算法模型的训练等均由主创团队相关人员选择与安排。涉案文章的创作过程与普通文字作品创作过程的不同之处在于创作者收集素材、决定表达的主题、写作的风格以及具体的语句形式的行为也即原告主创团队为涉案文章生成作出的相关选择与安排和涉案文章的实际撰写之间存在一定时间上的间隔。…涉案文章这种缺乏同步性的特点是由技术路径或原告所使用的工具本身所具备的特性所决定的。原告主创团队相关人员的上述选择与安排符合著作权法关于创作的要求,应当将其纳入涉案文章的创作过程。…从整个生成过程来看,如果仅将软件自动生成涉案文章的这两分钟时间视为创作过程,确实没有人的参与,仅仅是计算机软件运行既定的规则、算法和模板的结果,但软件的自动运行并非无缘无故或具有自我意识,其自动运行的方式体现了原告的选择,也是由软件这一技术本身的特性所决定。如果仅将软件自动运行的过程视为创作过程,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将计算机软件视为创作的主体,这与客观情况不符,也有失公允。因此,从涉案文章的生成过程来分析,该文章的表现形式是由原告主创团队相关人员个性化的安排与选择所决定的,其表现形式并非唯一,具有一定的独创性。…综上,从涉案文章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生成过程来分析,该文章的特定表现形式及其源于创作者个性化的选择与安排,并由软件在技术上“生成”的创作过程均满足著作权法对文字作品的保护条件,本院认定涉案文章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文字作品。”
从判决书表述来看,上面两个案例不同结果的主要区别可能在于:北京法院可能没有考虑(或者原告没有充分向法院证明或原告没有提出主张)原告设置检索关键词、审阅/筛选案件后聚焦2589个裁判文书的过程,仅是针对软件对收集后的数据的生成图形进行了分析;而深圳法院是将原告团队在软件生成文章前的各种活动纳入了创作过程。简而言之:前者仅对自动生成结果进行分析并认为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独创性;后者把人类在AI自动生成前的行为纳入为“创作”的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认为自动生成物是人类团队独创性选择素材后运行程序的结果。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Dreamwriter案例中,涉案文章末尾注明“本文由腾讯机器人Dreamwriter自动撰写”,但原告是腾讯公司。法院在认定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时的观点是“涉案文章在由原告运营的腾讯网证券频道上发布,文章其中的“腾讯”署名的指向结合其发布平台应理解为原告,说明涉案文章由原告对外承担责任。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涉案文章是原告主持创作的法人作品,原告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有权针对侵权行为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虽然腾讯公司将文章的署名给了“腾讯机器人Dreamwriter”,但最终主张文章著作权的主体还是腾讯公司。
笔者无意对两案作出过多评价,但作为法律从业者,笔者只是想说:这两个案件的不同处理思路,为司法实践中主张或反驳AI绘画著作权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例如:对于主张受保护方,尽量多的保留自然人在AI生成前/生成过程中的各种工作的证据,以证明AI只是权利人创作的工具或手段;对于主张不受保护方,则应强调AI即不具有权利主体地位,其创作生成内容的过程也不是使用者的智力活动或创作生成的内容已经脱离了使用者的控制和预期。
三、AI绘画对相关行业的挑战
笔者结合工作,对AI绘画在相关实务方面提出以下思考:
1.侵权问题
AI自己需要深度学习和训练。我们注意到,已有艺术家、画家公开、明确表示拒绝AI绘画数据库利用其作品进行训练和学习。因此, 如果AI绘画训练学习过程中使用的是仍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产品,AI绘画在构图、布局、线条、色彩等要素上与在先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或在保留了原作品的核心、基础表达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均存在使用AI进行绘画的主体构成著作权侵权风险。
另据报道:目前,AI绘画用户多为按照生成数量或者使用时间付费,但60%用户从未在AI绘画产品上有过付费行为,而在剩下的40%用户中,付费超过100元的也仅占比10%。[3]
因此,对于那些试图主张其对AI绘画享有原始著作权或者那些试图通过受让取得AI绘画继受著作权的,务必要厘清AI所绘图画本身是否有侵权风险,或出售作品权利一方本身是否会因其未进行付费而导致其未能取得该图画的完全权利。
2.社会认同问题
据报道,2022年8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办的新兴数字艺术家竞赛中,参赛者杰森·艾伦提交的AI绘画作品《太空歌剧院》获得了此次比赛“数字艺术/数字修饰照片”类别一等奖;而参赛者此前没有绘画基础,引发多方热议。
2023年2月,《白夜极光》发布情况说明,对AI作画公开表态,指出:“我们不会在我们的产品中使用AI作画,绝不希望合作老师提交使用AI制图的工作成果,绝不希望我们的合作方制作、使用AI作画的宣传物料。”其后,涉事画师公开表示歉意,并表示“后续…会将绘制的每张图的过程留存…”
3.上帝视角
实际上,ChatGPT的流行告诉我们,AI生成的内容与人类生成的内容在表达特征上越来越难以分辨。我们在讨论AIGC的权利人是谁、内容是否具有可版权性的前提是我们通过某种方式以上帝视角知道了AI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存在。而开篇美国版权局认为“Kashtanova女士是“本作品文本以及写作及视觉要素的选择、协调和排布的作者”的说法更充满了上帝视角和玄妙的气息。如果不是当事人的说明,我们如何去发现AI在相关内容中的作用?更不用说大多数版权登记机关系采用自愿登记的原则进行登记,登记只是形式性审查的结果。
同时,这些争议也提醒我们:相关组织者在组织筹办涉及绘画的展览、赛事活动中,或者在进行吉祥物、插画等征集活动中,是否需要在相关规则要求中对AIGC作出一定的说明或要求?AI软件的开发者是否可以通过用户协议中的格式条款对AIGC的财产权归属进行约定?就像摄影术的发明对再现性写实绘画的影响一样,技术的更新会引起对艺术以及法律的冲击。我们唯希望并相信:司法既不会阻碍技术(包括AI)的发展和价值,也不会过度稀释人类的权益。
后记:2023年3月16日,美国版权局针对AI绘画发布了新规,AI自动生成的作品,不受版权法保护,但是作者通过Photoshop进行创作的图片作品是受保护的。笔者将实时关注国内版权登记机构关于AI绘画版权登记的最新消息。








